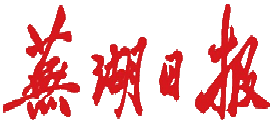走朱冲
平生最大的酷爱就是登山、看山、拜山、读山。
那天,也就是人间最美的一个四月天,天,是湛蓝的,风,是温馨的。与友人结伴,去攀援离城几十里地的红花山。上山有三条道,三个方向。我们选择从红花山东北方的朱冲登巅。
朱冲,位于红花山东北侧山脚下,这里居住多为朱氏乡民,系朱熹子嗣。1565年宋代理学家朱熹后人——十一世祖虎公携家眷由泾县迁居而来,于此世代繁衍生息,开枝散叶。
距朱冲八里地,撇开车辆徒步前往。像一个信徒对佛门虔诚的景仰,对山心存敬畏。虽未曾焚香沐浴戒斋三日,也不会三跪九叩行拜山之礼,却屏气静心沉淀浮躁,缓缓地顺着狭长的阳山冲,吮吸着山路两旁花草树木的馨香,聆听着山涧里潺潺流水和树上欢快的鸟语,向着大阳朱冲走去。渐渐地接近宁静安恬,宛若莲花的红花山,慢慢地享受着青峰列奇的大山,远远地溢出的温暖与慈悲。不由地一种惬然贯通肺腑,一种快感酣畅心灵。
在朱冲村口,凝神伫立在横卧村口溪沟上的紫云桥,回望石拱桥两端,一边紫云亭(宫)一边紫阳堂,这些依山而建,雄伟威严的古老建筑遗存,都来自久远年代的痕迹。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说,佐证它们的前世由来。
相传久远的春夏之交一日,晴朗天空突然乌云密布,接着一场罕见的暴风骤雨,霎时山洪倾泻而下,冲毁房屋、田地、人畜。
恰遇风水先生路过,指点惊慌恐惧的乡民,在村口溪沟架一座石拱桥,桥两端各造一座“紫阳堂”与“紫云宫”,镇住兴风作浪的“美人蛟”。从此,红花山和一桥一堂一宫,庇佑这里青山沃土朱熹子嗣,赐予这块土地上居民波澜不惊的寻常,过着尘世安定与轻盈的日月。
寻常日子与安定生活,被日寇的侵扰打破,这里成了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。陈木寿,这个福建宁德的汉子,1938年随闽东游击队来到皖南,3年后,在红花山区任独立排长,北撤前任皖南支队一营营长。抗日时期,他带领所属部队转战铜、南、繁、芜、宣、泾,令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胆颤心惊。
北撤前夕,他来到离村不远的一座山冈,这里掩埋着1939年5月中旬在乌金岭与日寇激战时牺牲的吴兴富、陈生春、彭寿明、钱志和、姚裕堂、强明金等六位战士。他在18岁小号手坟茔前,默默地伫立许久,这娃娃兵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,现在却长眠在异乡的山冈。他向当年为烈士装殓下葬的村民深深地鞠了一躬,然后毅然决然地领着部队,向长江边疾奔而去……
小号手与那些战死的新四军将士,以及驻扎这里的中共繁昌县委、皖南特委,还有驻守在红花山的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三营、在这一带活动的皖南支队的官兵,是喝着朱冲山涧里清冽的泉水,是吃着朱冲山地里的五谷杂粮,骨子里养成了炎黄子孙的硬朗与忠贞,为着民族的独立与解放,在繁昌抗战中心的红花山,在祖国的大江南北,“……用雪亮的刺刀,暴烈的手榴弹,火力猛烈的机关枪,前仆后继的冲锋……”
1948年4月,皖南铜陵、繁昌一带确定为“大军渡江跳脚板”,朱冲也被选定接应渡江先遣干部大队的“落脚地”。
这年的7月5日黎明,任三野南下大队干部中队长的陈木寿,从无为白茆洲偷渡,在繁昌油坊嘴登岸,他又一次踏上了江南的土地,来到阔别3年多的红花山脚下朱冲。
他在小号手坟茔前说:“快了,等大军渡江了,江南解放了,就带你回家。”话还没说完,就被凶煞煞的国民党独立十三旅密集的枪声打断。来不及吃上一口朱冲乡民准备的饭菜,就急忙率部隐蔽进红花山密林……
十六天后,陈木寿率部转战到南陵桂镇小青山,再次遭到国民党围剿,终因敌众我寡,陈木寿壮烈牺牲。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兵,竟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,在芜湖江边码头悬挂了三天。
就那三天,朱冲接连阴风怒号,霪雨霏霏。低沉的风声呜呜然,如诉如泣。村里上岁数的人都说,那是小号手吹的号。他们曾听过小号手为牺牲的战士下葬时吹过的号。指着村口一块巨大的巉岩,说小号手那几天,就站在那儿昂着头,举着铜号。
一看,那块巉岩还真酷似一个年轻的战士,昂首挺胸站在那里,背靠红花山,对着山外吹着号子。
想去墓地拜祭一下那小号手和另外五名英烈。村上人说,前几年,这些烈士忠骨移葬到了县老烈士陵园。
忠骨虽迁葬,可这些英烈热血与灵魂,早已融入了红花山这片青山沃土,融入朱冲这块山涧田地,庇护着这儿日益安逸富足的百姓。
山巅上
从朱冲村后一条崎岖的山道,登上红花山山巅。
在一千二百年前,佛家弟子曾经建造庙宇,宏扬佛法的遗地,如今重建的佛光寺前,仿九华山肉身殿前的九九八十一级石阶上,驻足不敢贸然上前。离红花山主峰红花尖,就差那么十来级的石阶。默默仰望一群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年轻人,争先恐后地登上山巅,成了山至高处人为峰。他们欢呼雀跃,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,指指点点。
毛泽东当年站在橘子洲头,一个哲学思想的高地,曾挥斥方遒,指点江山。敢仰天叩问:“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”,确立“到中流击水,浪遏飞舟”的浩然壮志。那是伟人的胆略与抱负。平凡的吾辈只有胸围,哪有如此大的胸怀。伟人重上井冈山黄洋界:“可上九天揽月,可下五洋捉鳖,谈笑凯歌还”,壮志凌云豪情万丈,又有谁敢与之比拟。
有人提议登山巅上一块平台,环顾四周苍苍莽莽群山,目睹远处浩浩汤汤江水,心中自会涌动潮汐。
清代繁昌知县梁延年,曾站在山巅,吟诵着:空山壁立对斜晖,影落寒江鸟乱飞。此处白云岩岫好,採樵人唱夕阳归……
那年,美国战地记者史沫特莱在江南新四军军营里生活了近一年后,去往江北新四军一线部队,通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和一个个据点,途经红花山。傍晚,她站在山巅,眺望云雾山岚万籁俱寂的山下,远处血色夕阳下一条奔流不息的万古长江。不久写下了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战歌》,在其中“横渡扬子江”一节里,记下曾夜宿红花山山巅,断垣残壁庙里的点滴。在书中,表达了对她一路护送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战士的热爱,描述了红花山奇峰峻岭的壮美,深信中国人民终会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……
抗战时期,为保卫皖南门户,阻击日寇进逼皖南,谭震林将军站在山巅,指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和皖南支队、游击队,在这里同日寇展开大决战,取得了繁昌第三次保卫战的胜利……
日军派遣军总司令曾哀鸣道:“国民党乃是手下败将,唯共产党军乃是皇军之大敌。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。”
震撼大江南北五次繁昌保卫战,打出中国国威,打出新四军军威……
最终没能登上山巅,是不愿当山高人为峰。盘膝坐在寺前石阶,面对一座释演湘大和尚圆寂后下葬的灵塔前合十祈恩。
多年前,登红花山山巅。那里还有红墙青瓦,翘角飞檐,紫竹扶疏,松柏参天的佛光寺。大和尚,还没回归本源清净的佛土,还在呕心沥血潜心修禅,为重建“佛光寺”,默默隐忍一路前行。在抗战时日寇炸毁的庙宇废墟上,搭起一间仅有几平米茅棚。佛祖前,大和尚双手合十:大悲无泪,大悟无言,大笑无声。还没开口求解,他又口吐几字:佛曰:不可说,不可说,一说即是错……
若干年后,尘世里一路跌跌撞撞,对一切事物的认知、感悟,懂得唯其靠自己心灵证得。
二千七百年前,孔子叹曰: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!
老子回道: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
孔子面对河流感叹,逝者如斯,自己年华老去,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
老子说:人,生于天地之间,和自然一体。人,生老病死,自然界的春夏秋冬,循环往复,是道的运动,大自然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。人得随遇而安,与自然和谐相处,不苦求功利,自己不被心所困,何来生出烦恼。
起身缓步拾阶下山,这佛门地境,本不属凡人久栖之地,还是回归红尘。遵循老子道的活法,过着上天赐予此生剩下的,寻常日月人间烟火:人生天地之间,乃与天地也。
下纸棚
从红花山主峰海拔450米高的红花尖顶,向西沿着山脊下到海拔269米高的乌金岭,再折向南,顺着两山之间山坳,缓缓地下到青棠冲纸棚自然村。
一幢幢拔地而起的住宅楼,依山而建,飞檐翘角红瓦顶,白墙灰裙红大门,错落有致地点缀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里。家家户户大门上方,有着一块十分奇葩的门牌:纸棚村。疑惑这村名从何而来。红花山方圆好几十里地,一座山头连着一座山头绵延不绝,漫山遍野修竹绿树层层叠叠,山间民居周围参天古树遮天蔽日。地名大多取冲、涝、头、凹、弯。这条山冲里却有着一座:纸棚村。环顾散落在绿树掩映中的民居,一条清澈见底的潺潺涧溪,找着与“纸”、与“棚”这两字具有共存关系又相互印证的参照物。
有一楼前晒场,一位耄耋老翁,正聚精会神编制竹器,是儿童跳舞蹈用的小竹篓,精美的小背篓下方,还吊上几串金色铃铛。
老人精瘦头发花白,饱经风霜的脸上一道道沟壑,是流淌过的岁月长河;那双温和的眼睛闪烁着慈祥的光芒,阅读过人间多少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满腹狐疑欲言又止,撞上老人那双黝黑深邃的眸子,似乎一下子就看穿了五脏六腑,湮没在心灵极地的蛛丝马迹,赤裸裸地暴露无遗。
老人娓娓道来;清道光年间,州府就在此设立了造纸工场。山上有大片的皮楷树林,山涧有长年不枯的溪水。生产出来的纸,色泽黄亮,纸质细腻,抗拉力强,耐皱耐折,吸水性好。是当时书画、印刷、装帧用的上等好纸。老人不无惋惜地长叹:皮楷树林毁了,原材料断供了,造纸技艺失传也没留存下来。村里仅剩一棵176年的皮楷树,遗留下一个造纸的纸槽,空留下一个带造纸的“纸”字,带工场棚的“棚”字的村名。
倏地穿越二百多年,站在高高的山岗,放眼四周,造纸作坊工场棚,散落在狭小的十里山冲。到处是忙碌的山民:煮树皮、碾料、造糟水、捞纸、压榨、拷干、晒纸、揭纸、数纸……也看到大山外府衙市井,文人墨客争先提笔,在这里制造出炉的一张张,坚韧洁白、柔软光滑、久存不陈的纱纸上,或泼墨作画或奋笔疾书……
在遗存下的纸槽前,在唯一仅存的皮楷树下,心存感激这纸槽这树木。他们的存世,胜过口口相传,甚至胜过地方志上的文字,有力地佐证着这里前世的辉煌与荣耀。
这几百岁的造纸槽,这一百多年的皮楷树,不问风月喜忧,不问花事朝落。只与淡默岁月守幽深。他们的存世,我们有了历史和文明的根,我们知道了曾经的过往,不惧怕时光摧毁和抑制,有了可传承的记忆,不再会忘却。
与这相距三十里地正南方的柯家冲,创建于五代的繁昌窑,兴盛于宋代,衰退于宋末元初,曾为南唐宫廷烧制过贡瓷,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它的衰败没落,就是在创烧青白瓷创造“二元配方”制瓷工艺后,就不再创新发展,就一直停滞不前,最终因落后而衰败灭亡。
当这里皮楷树资源枯竭,转而应采用这山山岭岭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竹资源。不幸的是,这里与“繁昌窑”的柯冲人一样,在历史不断进程与发展中,犯下错失持续创新的抉择。闭守等待的结局,只能是衰败、荒废……
纸棚造纸业的衰落、消亡,不必扼腕叹息,历史进程,客观规律,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。生存与灭亡,无非一种轮回,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法则。想到这,郁结的心便释然了。
程自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