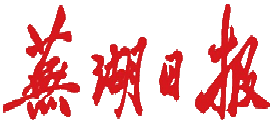秋色老梧桐,秋天宜看梧桐,宜听雨打梧桐。
以桐命名的树,最早知道的是泡桐,老屋的一角,粗粗壮壮地生长,开出淡紫的花,似乎经不起风吹,扑簌簌落到规整排列的鱼鳞瓦上,有婉约词的意境。如果花期遇到雨期,一番风吹雨打之后花瓣沤烂,碎瓷片一般,惨不忍睹。有一年夏日暴雨,这株泡桐如年迈的老者颓然倾倒,压在窄小的厨房顶上,折断的枝叶、碎裂的瓦块一片狼藉。另一种法国梧桐,在曾经的小学校园,入校园的长长的路畔,威武庄严地耸立着,叶间结毛球,等叶子落尽,毛球还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枝头,多了一抹萧瑟与寒意。
对于“梧桐”,和梅兰竹之类,常在诗词里相遇,面对文字,想象着它的伟岸、清朗。在《诗经》里,“凤凰鸣矣,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”,传说中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,树与鸟,相依相存。“其桐其椅,其实离离,岂弟君子,莫不令仪”,气宇轩昂的梧桐用来赞誉和乐宽厚的君子。
桐木,是制琴的好材料,东汉蔡邕从烧柴火的毕剥声中听出是梧桐木,抢救出尚未烧完的一段,制成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焦尾琴,桐木有幸遇知音,于是,焦桐成了流传千古的琴名。秋日里,总爱播放着管平湖的《梧叶舞秋风》,幽幽古琴声中感受梧桐的古朴清远,一叶知秋,它总是默然无语地传递着秋来的讯息……一直以为,梧桐,是诗词中美好的形象,是古乐中悠远的旋律。
秋风起起又停停,前几天刚有些秋意,转眼又重为闷热取代。午后外出,路上少闲人,专挑有绿荫的路前行。这条路东西走向,是出小区后的主干道,来来回回已经二十年了。去郊外看树,去公园赏花,对于绿化带里的草木却只是匆匆一瞥,开着碎花的紫薇、青青葱葱的冬青,被修剪得平整有序,看久了也不免乏味。间隔几米就有棵挺直的树,未曾想过是什么树,在我看来,被种在路边,端庄肃穆,风尘扑面,少了很多意趣。树无言、无争,种在哪儿就立在那儿,遗憾的是人有区别心,寻赏风景时往往忽略了身边的风景。取出手机,仰头拍照,百度后不禁一怔,像遇到了一位久仰大名而又无缘相见的人,此刻,这个人就在眼前笑而不语,二十多年来,日日走过梧桐身边而不知树名。
梧桐树干挺秀直立,没有旁枝错节,叶青碧一片,已经立秋,不见落叶,或许节气上的立秋如今已经不那么明了,等梧桐落叶,抑或要到白露的夜晚,或者秋分的凉风中?再次行于路畔,我立于一株梧桐树下,伸手抚摸,树干光滑、洁润,不似平日所看诸多的树皮黢黑粗糙,指尖触处,似一枚沁凉的古玉,又如浑朴的青色长缎裹于树干,这样的美好,才能担当起“乔木”的美誉,成为自先秦文学以来文学中傲然清俊的形象,多少年来,一直给予人荫泽。
夜来风雨声,梧桐更兼细雨,滴落而下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。是啊,岁月的流转,朝代的更替,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中,有着昂扬清逸之气的梧桐成了惆怅的寄托,空寂的后院,静得也只有秋雨滴落梧桐黄叶的声音,往昔的凤箫齐奏,春殿之中嫔娥鱼贯而列,翩然起舞,此时南唐的三千里地江河已是山重重,水迢迢,眼前飒飒秋风,烛残漏断,梧桐流淌着忧伤。这梧桐,不是南唐歌舞升平的宫殿院落中的梧桐,而是被囚禁于汴京的孤寂中的相伴。夜深无眠,无言独上西楼,斟了一杯又一杯苦酒,国破家亡的李后主身为阶下囚,以酒消愁,醉眼相望,泪眼婆娑,树影亦婆娑,千丝万缕的愁,亡国离乡的痛,无奈重门深锁,与梧桐同在的,是那一院深深的落寞啊!也可能只有高蹈超然的萧萧梧桐,才能载得起“故国不堪回首”的沉重的愁绪。
再次仰视这承接词人哀愁的梧桐,如大隐隐于市的隐士般立于车水马龙的街头,夜间的灯光将梧桐的树影斜斜地印在地上,如一册有着淡淡墨色的古帖,树下的我,品味着梧桐独有的意蕴。
梧桐,梧桐,一岁一枯荣,不久的清寒秋风中,一株株梧桐会卸下满树的繁华,桐叶会从枝头纷然飘落,在这岁月的流逝中默默生长。
张梅